近期中心姚彬彬副教授就所主讲的本科生通识课《中国禅宗思想史》接受武汉大学通识教育协会编辑专访,围绕以下六个问题,对禅宗思想及相关教学问题展开探讨。
问题一:请问您开设《中国禅宗思想史》这门课程的原因,为何从佛教众多分支中选取禅宗?
《中国禅宗思想史》这门通识课本是我的博士导师麻天祥教授早年所开设,后来麻老师年纪大了,逐渐淡出一线教学工作,所以我在2015年正式入职武大后,就把这门课接了过来,几年后申报了学校的通识课项目,由我主讲,麻老师仍是这门课程的指导顾问。
至于说为什么在佛教的诸宗派学说中选择禅宗思想来开设课程,个人也有一个相应的学术思考,即我认为禅宗是佛教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成熟的、也是最为理性化的阶段,禅宗扬弃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思想枷锁,汲取了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庄老道家(也包括儒家的一些成分)的思想内涵,成为一种高扬人的主体性,实现了佛教的自我“祛魅”的认识论和人生观。——至少就唐宋时期的禅宗思想而言,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有什么非理性或者崇拜虚假偶像的成分,较为彻底地抛弃了印度佛教的神秘主义思想底色。
传统的佛教信仰,特别是印度佛教,虽然与其他宗教相比,其理性思辨的成分确实还是多一些的,但毕竟还将一些金科玉律奉为圭臬,不容置疑,比如总要皈依“三宝”(即佛、法、僧),作为信奉者仍然会无形中进行自我矮化,总觉得世间有些神圣化的、甚至超自然的存在压在头上,将凡、圣之间的差距看得无限遥远。但惠能的禅宗则通过他的“创造性诠释”,把这个问题给化解了。《坛经》中说:“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在禅宗看来,所谓“三宝”,无非是要追求真理,走向自心的觉悟和清净之路,在心灵探索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中,并不需要崇拜什么偶像,"迷则佛即众生,悟则众生即佛”,众生与所谓“佛”的距离只在一念之间,这些思想,在唐宋时期许多禅僧的语录中都有明确表达。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惠能的禅宗强调“人性”与“人事”,走向入世,“因此唐代之有禅宗,从上是佛学之革新,向后则成为宋代理学之开先”。承先启后,是“佛教中国化”在古典时代的最终结晶。
近现代中国与当代日本的部分学者提出“禅宗非佛教”的观点,如果这个“佛教”指的是“印度佛教”的原教旨,那么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这些学者提出“禅宗非佛教”这个观点的出发点是要批判禅宗,认为禅宗背离了印度佛教的大方向,成了修正主义。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禅宗对于传统佛教的发展是超越性的,是中国文化对佛教的整体性重铸,实现了佛教的自我精神突破和思想革命,不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客观上已经成为一种相当理性的哲学思想,从而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二:如何让非专业的学生从经典中更好体悟到禅宗思想,付诸于人生实践中?或者说,禅宗思想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禅宗强调“担水劈柴,无非妙道”,他们所致力的自我超越之路,不是避世修行,而是在人情日用的正常生活中随处体认,所谓“平常心是道”。“平常心”在我们从事任何学习和工作生活中,都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心态,能够超越暂时性的得失顺逆,可以专注于日常所面对的一事一物的本身,摆脱功利性,以求道的精神做事,即今人所谓“工匠精神”。我经常以从事体育竞技项目,特别是用下围棋来说明这个道理(因为我自己就是围棋爱好者),如果在比赛的过程中患得患失、想赢怕输,那反而发挥不了正常水平,更容易输掉。——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比赛中专注地尽量下好每一步棋、找出自己能实现的最佳手段或方案而已,做其他任何事情也是一样,这就是“平常心”。
另外,我特别喜欢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形容禅宗的一句话,即:“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这是一种自尊自信、无所依傍的人格力量,不在人前矮三分,更不会被商业资本塑造出来的虚假“偶像”和“大师”们所迷惑,体认到真正的“众生平等”。用黑格尔哲学的术语来讲,禅宗思想显然已超越了一般宗教信仰中渗透的“主奴意识”,强调人的自我心力解放,“从来也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归根结底一切还是要靠你自己,实现了“自我意识”的彰显。
问题三:您的课程为何选取《六祖坛经》和《禅宗文化大学讲稿》作为阅读资料?
在佛教僧侣所建构的历史传说中,对于禅宗的创始人有多种说法,比如说是释迦牟尼开始的“以心传心”,在南北朝时期由菩提达摩传入中国。事实上,经过近现代学者如胡适、汤用彤、任继愈等先生的深入研究考证,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惠能才是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他的门人弟子们整理出的他的言论集《六祖坛经》,其中对于“禅”诠释,与此前佛教内部流行的种种说法有本质性不同,故胡适先生称之为佛教的“思想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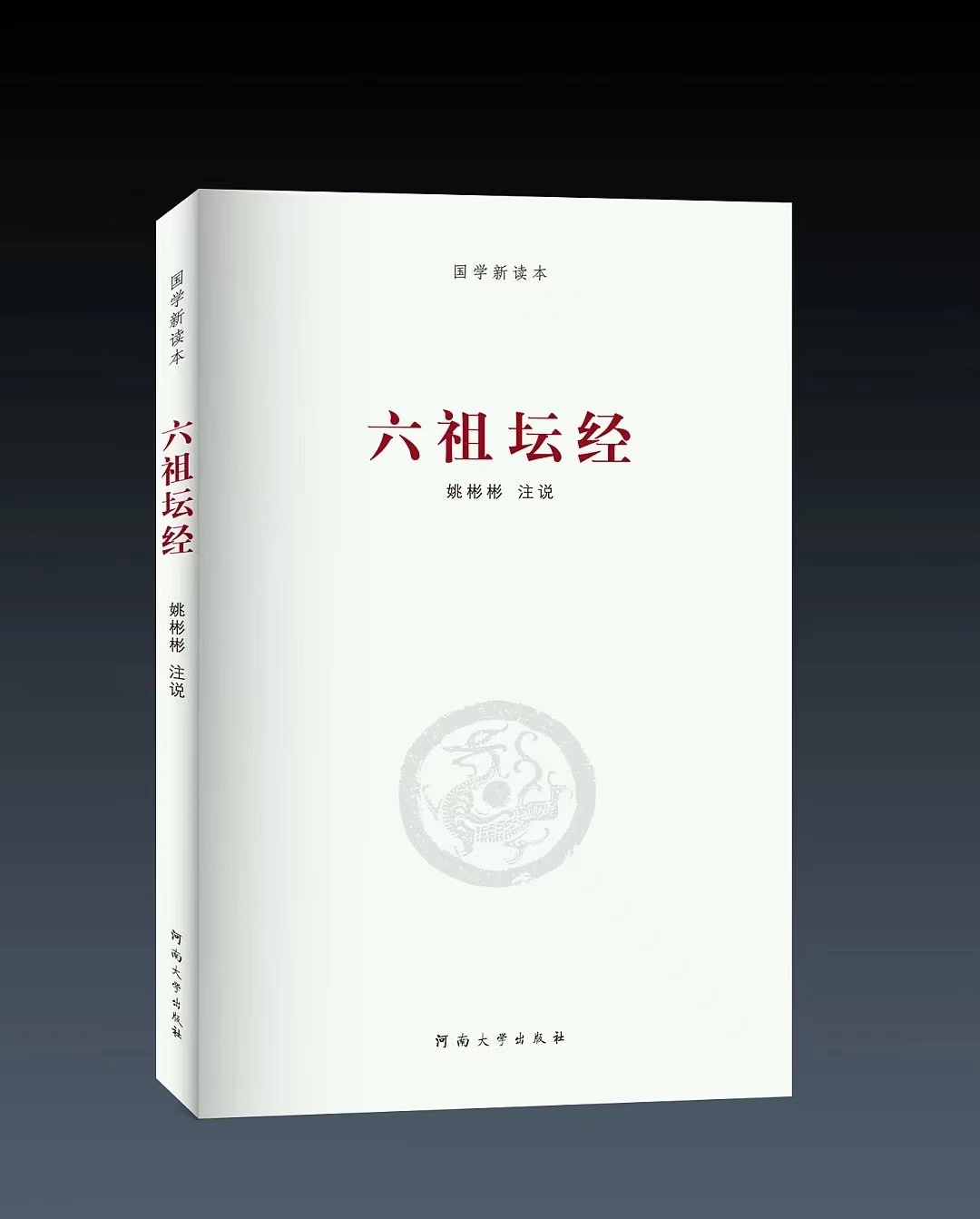
而且,《六祖坛经》中的思想论说,基本上已经标志了禅宗思想的定型,禅宗思想在惠能之后基本上没有本质性的思想发展,更多的是言说方式、教育方法上的花样翻新。所以,了解禅宗思想,《六祖坛经》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典籍。我自己也写过一册对《六祖坛经》进行解读的书,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其中包括七八万字的导读部分。——当然,我上课从来不要求学生去买我的书,尽量提供给他们一些电子版。
至于《禅宗文化大学讲稿》,是麻天祥老师当年为大学生读者编写的一本禅宗思想读本,将有关问题的思想源流脉络介绍得十分清楚,深入浅出。最为难得的是,麻老师始终坚持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角度探讨禅宗的种种学术问题,站在客观立场进行中立性的深入研究。

问题四:课程的讨论互动环节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问题?
在我的课上,课堂直接提问的同学不多,但下课之后的时间,以及有些同学加了我的微信,平时也会跟我有些交流。他们往往结合自己人生中的一些烦恼,乃至学习、生活、家庭以及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向我咨询,我感觉禅宗的思想观念,对他们确实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另外,有些同学由于平时接触过一些社会上对佛教的一般性的看法,有些神秘主义的倾向或认识,甚至曾经崇拜过一些各路所谓的“大师”(恐怕是“大忽悠”居多),在我的讲解下,大多可解决这些疑惑,了解更接近于历史原貌的禅宗思想,而不是社会上人云亦云的被神秘化的方面。比如,宗教界的僧侣们讲“禅”,无非开口闭口就是要打坐修行之类的,其实唐宋时期的禅宗思想绝非如此,无论是惠能还是他的弟子后学们,有许多明确反对“坐禅”这种神秘主义而又流于形式化的方法的论说。比如《六祖坛经》中说:“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惠能所诠释的“禅定”是一种在生活常态中不执著于外物和种种欲望干扰的精神境界,而不是去沉浸到潜意识世界去寻找什么超常经验;惠能的弟子南岳怀让则更明确说过,通过“打坐”去寻求觉悟之路,正如“磨砖作镜”,执着于追求神秘经验那是一种更大的执着,与禅的超越性精神南辕北辙。
问题五:您在教学过程中,对课程是否有过什么调整与创新?
这门课程跟之前相比,后来适当增加了一些关于介绍印度佛教思想学说脉络的内容,这样,一方面可以掌握禅宗的一些观念和术语概念的来源;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可以了解到禅宗和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佛教信仰有本质区别,摆脱了印度佛教中渗透的晦暗厌世的人生观底色,更解构了印度传统的那一套漏洞百出却又往往让人观之“不明觉厉”的繁琐哲学,从而呈现出精进乐观、入世和理性的价值取向。
此外,我在课堂上经常会结合一些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时事热点问题,作为案例进行剖析,试图更为生动具体地让同学们了解禅宗思想,那是一种活泼泼的精神,而不仅仅是书本上的一些知识点而已。
问题六:禅宗思想、佛教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何处?中国哲学如何能更好发挥现代意义?
当前佛教研究的学术界状况,坦率说,我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当下的不少学者过分抬高了乃至有意渲染传统佛教的那些繁琐哲学,而且还有一些跟风赶时髦的倾向。比如西方学者的佛教研究传统,较为重视梵文、巴利文乃至藏文佛典,现在许多国内学者也按这个路子去搞,当然这不是没有价值的,但应该了解到,世界佛教的各语系典籍中,汉译佛典保留的文献最全面,而且定本也更早一些(比如现存梵文佛典许多来源可疑,而且基本上都成书于11-17世纪间)。西方学者之所以形成那个路子,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中多数人阅读古汉语文本有困难而已。——中国学者本来也有自己的优势,但如果抛弃这一优势,跟着人家的路子走,恐怕未必是可取的,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可以参考借鉴,但完全去模仿人家,那就是邯郸学步了。日本学者过去做的好一点,但现在的情况也不好说了。
上面这些还是见仁见智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论问题,当前让我最不以为然的情况是,许多人的研究是“佛教本位”,研究什么说什么好,站在佛教自身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高度上看一切问题,甚至出于现实利益或其他什么的考量,有意去神化已故甚至健在的某些佛教僧侣,这样很难得出客观的、更具备宏观开阔视野的研究结论。比如我最近看到的一篇论文,简单把近现代的佛教研究大家分成拥护佛教和反对佛教的两派,这种划分毫无意义,因为就近现代的那些学者而言,即使有些人对佛教没什么好感,但也做出了非常卓越的研究贡献,如果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中,是很不科学也很不客观的。
我的太老师任继愈先生生前曾经说过:“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正像马克思说的,跪着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难以保持客观。”对此我有较多认同,不过也不能否认,即使在各个宗教内部,也经常会出现态度相对客观理性的“学者型的信仰者”。学术研究,特别是针对宗教问题的研究,更要注意立场的客观性。——因此,如果回答“佛教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问题,我觉得强调“客观性”最为重要。
至于“中国哲学如何能更好发挥现代意义”这一问题,我个人的体会是,中国哲学中讲“真、善、美”的问题,在世界哲学之林独树一帜,当然这不是说西方哲学或其他哲学不讲这些,而是中国哲学讲得有自己的明显特色,在这些问题上更重视落到实处,重视实践,在中国古典哲人看来,不能身体力行的知识那就不是“真知”,由此,“真、善、美”才能内化到自己的精神生命中,开显出更为高远的人生境界。
此外,单方面讲“真、善、美”恐怕是不行的,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学说都没有去弘扬“假、恶、丑”的,单方面讲,往往就成了令人厌烦的说教,所谓“正确的废话”,像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包装了国学或佛学外外衣的“心灵鸡汤”,大抵是这类货色,本质上其实成了“阿Q精神的哲理化”。
因此,“真、善、美”的开显,必须建立在对“假、恶、丑”的批判之上,才能更活泼、更有意义地彰显出深刻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此方面蕴含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比如禅宗本身对神秘主义和虚假偶像崇拜的批判;儒家立足“道统”意识对古代王权专制的“势统”的批判;道家强调“见素抱朴”,以真朴自然的境界为追求指向,这也是对文化现象中一切虚伪、虚假成分的批判。
我早年阅读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相对多一些,非常服膺这一哲学传统中所开显的“否定”精神,对于世俗文化、流行观念,始终应持有一种客观冷峻的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儒家所谓“中庸”与佛家所谓“中道”,都不是无可无不可的“乡愿”或一味“圆融调和”,讲的是超越各种偏见而能客观地把握事物的本质。我认为这就是当前中国哲学应具备的现实关怀和开显其深刻意义之要领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