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说同异问题争议的回顾与辨正
——兼论清代乾嘉学派历史主义向度的思想渊源
姚彬彬
刊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姚彬彬,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现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已出版《现代文化思潮与中国佛学的转型》《“章门弟子”缪篆哲学思想研究》等著作6部,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章门弟子’缪篆哲学思想研究”“《周易》诠释与清代新义理学的思想源流”等各级课题6项,多次获省部级科研奖项。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佛教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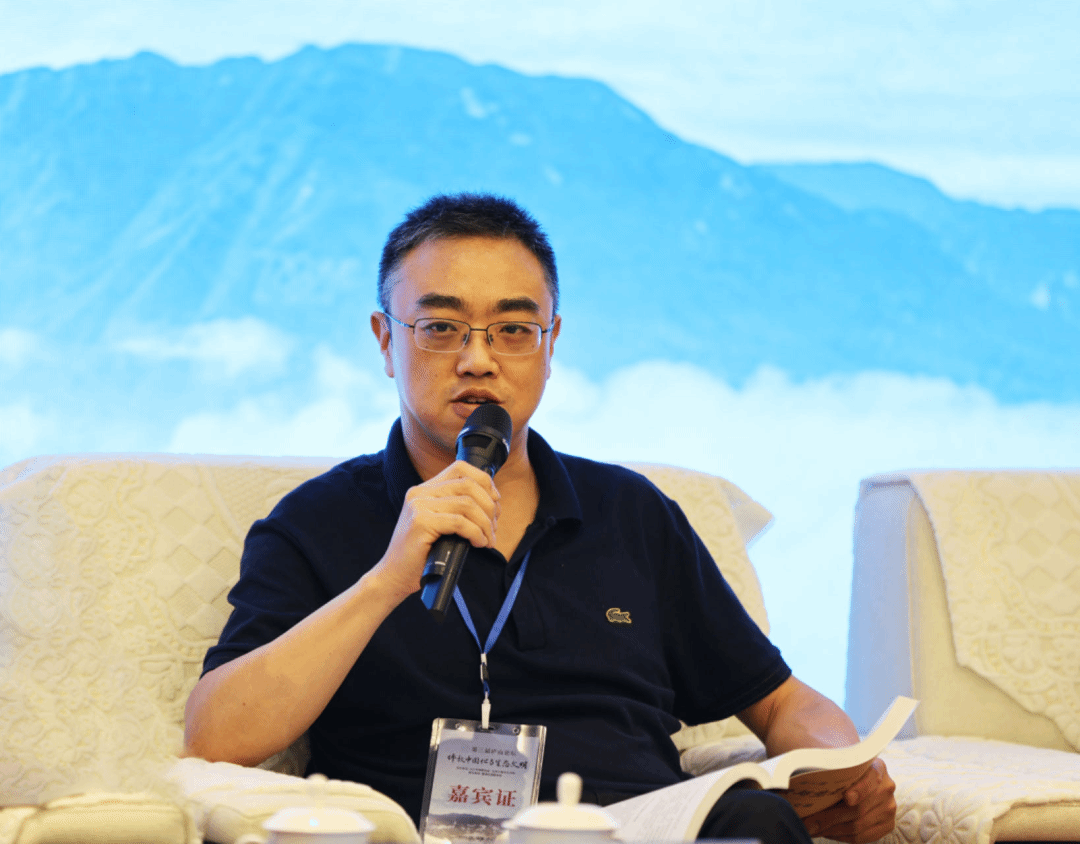
摘要:清代学术于今古文经说的对立意识肇端于19世纪以后的今文经学倡导者刘逢禄等对古文经学的攻讦,并在晚清以降成为重要思想议题。周予同基于廖平对于今古文经学不同宗旨的辨析,分判二家对立观念之要点,当代学界对其说提出颇多异议。回顾汉代经学今古文经说的实际情况,可见当时在有关观念上二家虽尚未形成非此即彼的分野,但已蕴含了一定倾向性。这些倾向虽被清代今文经师们逐渐绝对化了,但并不能完全否定这些倾向本身的存在。乾嘉学派对于东汉古文经师的历史主义倾向的认同奠定了其发展走向,同时历史主义亦构成清代乾嘉学派的思想底蕴。
关键词: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乾嘉学派;历史主义;廖平;章太炎;周予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周易》诠释与清代新义理学的思想源流”(21FZXB015)
关于清代学术的基本宗旨路向问题,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概括为从清初的“经世之学”到乾嘉时期的“经史之学”的演进,其中存在内在逻辑理路。劳思光提出,清儒顾炎武、黄宗羲诸家皆以通经致用为理想追求,以“外而治平,内而成德,皆须求其道于六经”,故“‘致用’必恃‘通经’为基础,然则‘通经’之工作要点何在?此处显然首先涉及一严重问题,即所谓‘经’者本身之内容及解释有无定准;此问题倘无明确答复,则经本身尚无定解,如何能据之以求治平之用乎?于是由‘通经’乃须转往‘考古’”,最终“再进至建立客观标准,以训释古籍,此即由清初学风至乾嘉学风之演变过程。而当客观训诂标准建立时,乾嘉学风即正式形成矣”。余英时则认为,代表清代学术风气的乾嘉之学这种追求“客观标准”的价值取向,“它与西方19世纪兰克以来的‘历史主义’在精神上确有其契合之处。清人之考订个别事实与辨别材料真伪,与西方的‘历史主义’取径尤为近似”。“历史主义”(historicism)兴起于西方18世纪末叶,其基本观念是,人类社会的一切价值、观念和行为,都存在其客观的历史性原因和背景。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历史的‘发展性’(development),以为事件和事件之间具有相互的连锁关系,因此历史的过程有着不可分裂的连续性质(continuity);人们如果想完全了解一件史事,则应追溯至起源部分,始能有全盘的领会”。这一思潮至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集其大成,如兰克之名论谓:“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人类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所思所为,这样就能发现,除去道德观念等恒久不变的主要理念之外,每个历史时代都拥有其特定的趋势和自己的理想。既然每个历史时代都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价值,因此人们也不应忽视时代的产物。”要之,对于一切历史事件、人物乃至种种观念,均旨在溯源观流以明其递嬗之迹,基于客观性旁观者的立场进行梳理描述,而不作任何价值裁断(这一点也是历史主义在20世纪以来遭到后现代主义者们强烈批判的根本原因),即历史主义所持之要领所在。而清代乾嘉之学的特征,作为斯学之“殿军”的章太炎总结说:“大氐清世经儒……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 并总结治学要领为六点:“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重在求得古经古义之本来面目,重视充分的证据和理性的分析裁断,断除情感之干扰而不做主观评判(风议),凡此种种,确与兰克之历史主义观念若合符节。此种学风之形成,可溯源至汉代经学的精神传统;清代学术“致用”与“求是”宗旨之分野,更与经学今古文之争这一旧案直接相关。兹针对晚近以来有关此问题的种种争议,略作爬梳辨正。
一、清代后期今古文经学之争的重启
汉儒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经学盛于西汉,古文经学渐兴于东汉,二派之间,势同水火。至汉末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世称其学为“通学派”。自此而后,今古文二派均有不少重要典籍逐渐亡佚,所谓“今古文之争”在中国经学和儒学史上亦不再构成重要问题。直至清代中叶以降,旧案重翻,再起波澜。
清代学术的主要议题,本系“汉宋之争”,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但“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所谓“汉学”指取法汉儒名物训诂、典章制度之说的考据学(朴学);所谓“宋学”即承继宋明儒的义理学。清学早期的大师之一惠栋始立“汉学”之名,其再传弟子江藩撰《汉学师承记》,列汉学学者五十六人,又撰《宋学渊源记》,列宋学学者三十九人,严格划定汉宋之别的畛域,壁垒森严。不过,清代的汉学一系学者,本无今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对此,后来分别主张今文的康有为,与推崇古文的章太炎,均有共同认识,康有为于1891年致书朱一新时说:“国朝顾、阎、惠、戴诸人用功于汉学至深,且特提倡以告学者,然试披其著述,只能浑言汉学,借以攻朱子,彼何尝知今古之判若冰炭乎?不惟不知其判若冰炭,有言及今古学之别乎?”章太炎亦谓:“清初诸人讲经治汉学,尚无今古文之争。自今文家以今文排斥古文,遂有古文家以古文排斥今文来相对抗,孙诒让作《周礼正义》,专重古文,与今文为敌,此其例也。”
然乾嘉以降,汉学考据之风渐成学林主流,其中不少学人惟务纠缠于经书中一字一句的释义,贬低义理之学为虚妄不实,而本身却流于“碎义逃难”。刘师培曾总结说:“自征实之学既昌,疏证群经,阐发无余。继其后者,虽取精用弘,然精华既竭,好学之士,欲树汉学之帜,不得不出于丛缀之一途,寻究古说,摭拾旧闻。此风既开,转相仿效,而拾骨积襞之学兴。”而宋明儒之义理,又多被时人视为濡染佛道二氏之臆说,遂有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宋翔凤等倡《公羊传》等西汉今文家的“微言大义”之说,皮锡瑞《经学历史》中总结其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榖》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继其学者后又有魏源、龚自珍,乃至清末廖平、康有为等。他们号称“复西汉之古”,实为旨在探寻经学中能够经世致用的元素,以纠乾嘉汉学末流饾饤琐屑而枉顾大道精义的偏失。
清代主张今文经学的较早诸家中,庄存与、孔广森倡《公羊传》之“春秋大义”,然并未于古文经学专致非讥,重启汉代今古文门户之争者实为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其鼓吹“左氏不传《春秋》”之说,以古文经典《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同类,本与孔门《春秋》无关,且经刘歆窜改,认为《公羊传》才是理解《春秋》的正宗。宋翔凤撰《汉学今文古文考》则不仅指责刘歆窜改古文典籍以充儒门古文经传,还借此依附王莽,全盘否定了东汉古文经学的合法性:“当时学者,惟杜林、郑众、贾逵、服虔、许慎、马融、郑玄诸家好言古文。其书之传者,惟许、郑两家。许慎《说文解字》引古文经以证六书,郑玄辄以古文读正今文之字,知古文家专明训故,其谭先王之制、为政之体,非博士所传,不可依也。”其学唯以西汉所立今文十四博士之经说为准,拟从根本上颠覆“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的主流学风。稍后的龚自珍、魏源皆有类似说法,此即近代廖平、康有为极力鼓吹的“古文经为刘歆伪造”之说的前承渊源。
故晚清之所谓“古文经学”者,实为清代汉学之“正统派”后学于此一系今文经学倡导者攻讦之应对,从而重新建构了古文经学之学派的认同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心目中的清代古文经学,用西方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可称之一种“被发明的传统”。章太炎于此亦不讳言,故其称:“自今文家以今文排斥古文,遂有古文家以古文排斥今文来相对抗”云云,其弟子钱玄同甚至说:“从郑(玄)学以后至章君(太炎)以前,没有一个古文家。或目郑学者与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诸氏为古文家,则大误。”此非无因之谈。然乾嘉汉学的精神谱系中是否蕴含汉代古文经学的某些要素,则尚有进一步探讨之余地。
二、近代以来今古文经学对立观念的建构及其是非
刘逢禄、宋翔凤等开启了清代学术关于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意识,而落实到种种思想观念的具体分野上,肇其端者实为近代的廖平。廖平延续清代今文学者有关古文经为刘歆窜改之说,更坚信《周礼》为刘歆所伪造,其谓:
刘歆官司儒林,职掌秘籍。方其改羼《佚礼》以为《周礼》,并因博士以“尚书为备”一语,遂诋“六经”皆非全书。……如《七略》之有《周礼》、《左氏》、古《书》、《毛诗训诂传》,此刘歆所改。
以《周礼》为刘歆据所见前代礼学典籍所伪作,并将之充作六经之“礼经”;此外若《左传》《古文尚书》等古文典籍,亦经其加工而面目全非。廖平认定,刘歆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通过古文经来树立周公的崇高地位,因有周公摄政之例在先,以之为王莽摄政乃至篡汉提供合法依据。刘歆树立古文经的办法,是攻击今文“五经”残破不全。故廖平断定:“所有‘古文家’师说,则全出刘歆以后据《周礼》《左氏》之推衍。又考西汉以前,言经学者,皆主孔子,并无周公;六艺皆为新经,并非旧史。”廖平之说直接启发了康有为1891年梓行的《新学伪经考》的核心观点:“‘伪经’者,谓《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新学’者,谓新莽之学。……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乃谓古文经全出于刘歆一人之伪。康氏弟子梁启超、陈千秋亦参与《新学伪经考》之成书,后梁启超亦坦陈乃师持论过分主观,为了抹杀不利证据,康有为“乃至谓《史记》《楚辞》约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清代以降今文学者以古文经为刘歆窜改乃至全盘伪造之说,其实大有“阴谋论”味道,其考据论证十分勉强,已逐渐被后来的学者否定。因为,刘歆之倡导古文经,早在王莽主政以前。《移书让太常博士序》云:“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议,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汉书·楚元王传》亦载其事,此即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撰述之缘起,其文述古文经之发现始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若事实真如廖平、康有为等所言者,同时代的“太常博士”们完全可以明确揭穿而据理驳之,却何以“不肯置对”?这种阴谋论的建立,如章太炎所说,实为“以意见诬之,其读书而未论世乎”。至1929年,钱穆撰《刘向、歆父子年谱》,于刘歆生平事迹详加考辨,揭出28条史实性的坚实证据,证明刘歆并无为古文经作伪的机会和动机,堪作定谳。
廖平在其成书于1886年的《今古学考》中的《今古学宗旨不同表》辨析今古文经学各方面的观念之分野对立,总结为33条纲目;周予同于1925年完成的《经今古文学》中依据其说,并加以精炼简化,勒定为13方面。周予同之说被后来有关中国思想学术史方面的著作多所采纳,影响深远。具体见表1。

不过,周文始问世时,钱玄同便表达过不同意见,他认为:“友人周予同兄之《经今古文学》,我也以为不对,因为他的见解是‘廖倾’的,而且他不仅要析汉之今古文‘学’,还要析清之今古文‘学’;而且他竟认所谓清之今古文‘学’与所谓汉之今古文‘学’是一贯的:这都是弟所反对的。”钱氏认定,汉代今古文经说间本无本质性的分歧,其《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文中说:“至于经说,则古文家与今文家正是一丘之貉耳。两家言作《诗》本义,言古代史实,言典礼制度,同为无据之臆测,无甚优劣可言。因为两家都是要利用孔子以献媚汉帝,希得到高官厚禄者,故都喜欢说孔子为汉制法,都喜欢谈图谶纬候。古文家之异于今文家者,仅在孔子以前又加了一个周公。这是因为古文家的始祖刘歆欲献媚新帝王莽,因周公摄位之传说最适宜于作王莽篡汉时利用的工具,故古文经说到处要抬出周公来。”当代不少学者重新重视钱玄同此说,以周予同之说多以清代今文经师的看法附加到了汉儒身上,认为汉代今古文经学本无如此清晰的观念分野。这类看法相当有道理,但似亦有矫枉过正之处,因为,虽汉代今古文经学在有关问题上虽未形成非此即彼的认识,但周予同所总结出的许多问题,在汉代二学派间确已形成一定的倾向,这些倾向虽被清代以降的今文经师们逐渐绝对化了,但并不能完全否定这些倾向本身的存在。
首先,周予同以今文家“崇奉孔子”、古文家“崇奉周公”,实则汉代今古文经师皆尊孔子,今文家以孔子为“素王”受命,古文家于此说亦无异,但古文家于孔子、周公并尊,此为与今文经说之不同处。
孔子为素王之说,始见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见素王之文焉。”古文家亦时有类似说法,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亦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此皆古文经说。刘歆之父刘向《说苑·贵德》亦云:“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即使非专治经学的王充,其旨在“疾虚妄”的《论衡》亦多言“素王”,若《定贤》篇云:“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所谓“素王”者,以孔子有王之德而无王之位,此为汉儒之通义,无分今古。古文家疑“素王”之说者始于魏晋,杜预《春秋序》云:“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周予同之说亦有所本,盖据后世之说以律汉儒耳。
然汉儒之古文家较之今文家而言,确实更强调周公地位的重要性。王莽摄政时,刘歆以古传《周官经》之书易名《周礼》,立为学官,置博士。廖平、康有为等以其书为刘歆窜改或伪造,并无所据,该书被发现的记载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言得于民人李氏。贾公彦《周礼正义序》云:“《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刘歆谓《周礼》为周公创制,以之向王莽改制提供蓝本;而周公摄政亦史有明文事,刘歆所行,固未尝无为王莽摄政提供合法性依据之意图。另据黄彰健考证,《尚书·康诰》中“王若曰”之语,汉儒古文经说以“王,周公也”,意指周公摄政称王(今文经说以“王”为周成王),此说亦导源于刘歆。《汉书·王莽传》记王莽奏太后事:“《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直接援引此说为篡权典据。汉代今文经师编造孔子“为汉制法”之说,此为《公羊》家所常言;而古文家之更尊周公,以孔子“述而不作”,亦在无形中消解了这一论证汉代“君权神授”之合法性的政治神学观念,王莽何以不遗余力地倚重刘歆,扶植古文经学,由此可得其解。
孔子尊周道,以周公为精神寄托,本系史实。《论语·八佾》中载孔子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称美周公之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晚年时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故汉代古文经师推重周公,本系儒门古义,自非虚构,王莽之于古文经学,实为相互利用的关系(王莽本人亦有古文经学的传承),不能说只是刘歆等主观性的一意攀附。
其次,周予同以今文学信纬书,古文学斥纬书为诬妄,此说可能有些极端,因为汉代古文经说亦不乏兼采纬书之例;不过,总体地看,古文家之于纬书,确实不乏持一定保留态度者,意见相对更为理性。
周予同此说当本于《隋书·经籍志》:“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然今人考汉世之古文学者,自刘歆以降,亦多涉谶纬。即使号称“通学”而实倾向于古文的郑玄,对谶纬亦有较深研究,“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肤色、臭味、道德。并将帝王之系统及国家之制度,纳入其中”,并多为纬书作注。实际上,周予同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汉代五经家,不仅今文学家与纬谶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古文学家及混淆今古文学者,其对于纬谶,也每有相当的信仰。”虽然“古文学家以六经为史料,专究声音训诂之学,本可自脱于诬妄的纬谶”,“古文学在学统上本与纬谶立于相反的地位。但汉代古文学者,因为或阿俗学,或投主好,或别具深心,所以也多与纬谶有关”。此说大体可从。
程元敏查考东汉诸儒著述,统计“非谶者”之情况,仅得九人:“东汉君主初假谶纬以立位,既而欲假谶纬保国,故勠力提倡谶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者矣,是以天下靡然响风。其间固不乏有识之士,若桓谭、郑兴、尹敏辈,倡言反谶,然卒以沉滞,或仅以身免。此辈儒者,史传所载,不过九人,别六人为贾逵、王充、孔季彦、张衡、杨充、荀爽。”此九人或本为古文经师,或系倾向于古文经说者,其中贾逵的情况颇具典型性。
以往学界多以贾逵颇习谶纬,依据是《后汉书·贾逵传》中多言其事,其实这是他以学术为工具的生存手段,程元敏指出:“贾君据《左传》,照以图谶,明刘汉承尧后,以火德王,详《集解》(文繁不必录)。贾君阿谀媚上,冀得宠禄,实非附谶。《后汉书·贾逵传》论曰:‘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李注:‘贾逵附会文致,谓引《左氏》明汉为尧后也’。”然贾逵的本来学术思想取向,并不以谶纬为然,“贾逵尝著文专论谶文之失,张衡上疏曰:‘谶书……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执若无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后汉书》本传)此贾君指擿谶书中一卷之中述事互异”。此亦可印证于前引《隋书·经籍志》所言贾逵诸儒以谶纬为“妖妄”之言。贾逵曲学阿世,其行自不足取,然由此实可见汉世古文家之颇言谶纬者,此种“违心”的情况当不在少数。
查周予同据为蓝本的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言,本谓“今多主纬候”,“古多主史册”,未言二家对待谶纬问题有非此即彼的本质区隔,只是所重者倾向不同,当较切近历史真实情形。
最后,周予同以今文学为经学派,古文学为史学派,此说沿袭廖平;考诸汉代今古文二派诠释诸经之风格,似无如此明显之分野,然于《春秋》经说而论,古文家确实更倾向于“历史主义”,并影响了后世对孔子形象的重新诠释。
因《古文尚书》亡佚(今存者为《伪古文》),《礼经》今古文所宗文本不同,汉代今古文《易》学皆宗象数,情况极为复杂,兹以情况较为明晰的《诗》说为例。从今存古文典籍《毛诗》看,其与今文派之齐、鲁、韩三家所阐之经义,并无本质区别。今古文四家《诗》学,皆本于《孟子》所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以儒家的政治理念诠释《诗经》,“于是,一部绝美的文学书成了一部庞大的伦理学”。如今文《鲁诗》之说,《汉书·杜钦传》:“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据颜师古注,此据《鲁诗》为说。而《毛诗》之说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尽管《毛诗》倾向于赞颂,《鲁诗》倾向于讽喻,然意旨大体近似。今古文家皆以《诗》中微言大义教化君民,虽皆常援史事为说,但显然都是典型的“经学”,并无史学意味。今文三家《诗》说,惟《齐诗》好采阴阳五行之说附会《诗》义,近战国齐地阴阳家之风,汉儒更多援谶纬为说,而《鲁诗》《韩诗》与《毛诗》,则均无此弊。由此可见,就《诗》学而论,以“经学”“史学”为今古文经说之分野,似有抵牾。
今古文诸经之经说间,惟《春秋》之学可按周予同的意见进行划分。今文派的《公羊传》与《榖梁传》偏重于“义”,强调掘发使“乱臣贼子惧”的“一字褒贬”;而古文派的《左传》虽非完全不讲“义”,更重于“事”,旨在以史传经,正如徐复观所说:“惟左氏论书法,很少采用一字褒贬之说。说孔子以一字表现褒贬,这是《公》《榖》最大的特色……皆可概称之为‘以义传经’。而左氏……更重要的则是‘以史传经’。以义传经是代历史讲话,或者说是孔子代历史讲话;以史传经则是让历史自己讲话,并把孔子在历史中所抽出的经验教训,还原到具体的历史中,让人知道孔子所讲的根据。”就今古文二派之《春秋》经说而言,以今文为“经学派”,以古文为“史学派”,还是说得通的。
《左传》之学,本倡于刘歆。《汉书·楚元王传》云:“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刘歆早年曾从翟方进、尹咸学习过民间传本的《左传》,后来领校中秘书时发现了秘府藏本,认定“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榖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以《左传》更可靠,远胜于《公羊》《榖梁》二家。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举古文经籍,亦以《左传》居首,在他的长期坚持下,到了王莽摄政时期,《左传》等终于被立于学官。侯外庐等总结汉代经学的今古文学派间:“就经说的内容说,常以争立《左传》为其中心问题,即是争论各派《春秋》说解的优劣问题。”程元敏亦认为:“诸经门户之争,莫烈于《春秋传》,亦莫繁于《春秋传》。”徐彦为何休《春秋公羊传序》所作疏中说,东汉时郑众“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专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贾逵亦“作《长义》四十一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至东汉末,何休试图重振《公羊》之学,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批判古文经说。郑玄起而抗辩,针对何休三书,作《箴膏肓》《发墨守》《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最终的情况,如《左传》孔疏云:“至郑康成,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榖梁废疾》。自此以后,二传遂微,《左氏》学显矣。”
《左传》载史记事,极少玄虚不经之谈,亦罕见今文家针对《春秋》经文“过度诠释”之风,而西汉所树立的孔子之神格形象,正是基于这种对经文的“过度诠释”乃至比附于谶纬迷信之说。通过《左传》来理解《春秋》,以孔子为传承三代文化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先师”,实为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古文经师们虽并未直接否定今文经学所建构出的富含宗教神圣性与神秘色彩的孔子“素王”形象,也已在客观上对之进行了弱化,这由传《左传》学的杜预《春秋序》之所述已可见诸一斑: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魏晋时期儒家经学不再成为社会主体文化,而以玄学代之,在魏晋玄学的叙述中,虽亦以孔子为圣人,却又往往与老庄并论,这显然是将孔子的形象由“神”还原为“人”的过程,汉末古文经学(特别是《左传》学)对于孔子形象在一定程度的“祛魅”,实已开其端绪。
就此而论,两汉今古文经学彼此塑造的孔子形象,实与古印度佛教的“上座部”与“大众部”所塑造的佛陀形象,相当类似。“上座部”以佛陀为觉悟的“人间导师”,并不强调其超自然面相;而“大众部”(大乘佛教之前身)则致力于神化佛陀,使之成为全知全能的神格。就此而论,东汉以降古文经学之勃兴,实有类于汤用彤所称之“反求圣经”之思想运动:“大凡世界圣教演进,如至于繁琐失真,则常生复古之要求。耶稣新教,倡言反求《圣经》(return to the Bible)。佛教经量部称以庆喜(阿难)为师。均斥后世经师失教祖之原旨,而重寻求其最初之根据也。夫不囿于成说,自由之解释乃可以兴。思想自由,则离拘守经师而进入启明时代矣。”至少对比今文经学极为明显的神秘主义倾向,古文经学在某些问题上较为倾向于历史主义,虽然在两汉时期表达得可能尚不明显,但其中已多少蕴含了后世中国经学逐渐走向思辨理性的源头活水。
三、清代学术历史主义向度的汉代古文经学思想渊源
清代具备时代特征的主流学术潮流即乾嘉汉学,“汉学”实即“考据学”之别称。漆永祥指出,清代以降称“考据学”之名众多:“如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常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等人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近今人则多称为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清儒追溯汉代郑玄为斯学之鼻祖,《四库全书总目》于郑方坤《经稗》条目谓:
汉代传经,专门授受,自师承以外,罕肯旁征。故治此经者,不通诸别经;即一经之中,此师之训故,亦不通诸别师之训故。专而不杂,故得精通。自郑元(玄)淹贯六艺,参互钩稽,旁及纬书,亦多采摭,言考证之学者自是始。
郑玄解经虽基于古文派立场,但并无明显的门户之见,旁通兼采,善于利用不同文献进行相互比勘。张舜徽于《郑氏经注释例》中总结郑玄注经体例,计有循文立训、订正衍伪、诠次章句、旁稽博证、训声、改读、改字、征古、证今、发凡、阙疑、考文等,这些其实也正构成了清代考据学的基本要素,清儒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规范更为完备、推理规则更为严密的治学方法。
由于乾嘉汉学宗法郑玄,而郑玄之学虽宗古文经说,亦采今文,又兼信谶纬,故世称“通学”。这一客观情况,应是今人质疑廖平、周予同等划分今古文学派分野诸标准的根由所在。实际上,黄彰健早年在《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著中已对此问题有很好的解释:“郑玄、王肃皆治古文经学,而古文经学本不贵守家法……今文经学贵守家法,此则由于博士弟子需参与考试,需据博士师说为答案,此乃利禄之途使然,并非追求真理所应为,故当时通人即斥习今文经学之儒生为俗儒。”“东汉时古文经师之释经,注重字指及声类训诂,其立说贵于经文信而有征,其立说不拘一家,而唯求其至当,其治学方法本较今文经师为胜。而古文经师所据之材料古,解说亦古……这种求真理的热忱,更可感动人,使人更尊重古文经学。”至于郑玄信谶纬,“信纬为孔子所作,这是他贪奇好博,不如他以前之古文经师处”。要之,东汉之古文经师治学兼采今文乃至谶纬之说者,其例不胜枚举,这是由于他们本无明确的门户意识;而今文经师治学则断然不采古文之说,直至清代之今文学者,亦大体如是。
汉代古文经学之滥觞,本源自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他是汉景帝的第二子。《汉书·河间献王传》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班固称赞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此语构成汉世古文经学的基本准则。若郑玄曾有其治学之名论:“天下之事,以前验后,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此种基于怀疑意识而旨在求是之精神,于汉世古文经师的群体中虽未必被明确树立为旗帜,实早已构成潜在的方法准则。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在治学实践过程中尚未能全然摆脱种种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谶纬迷信观念,此亦不必讳言者。
就清代乾嘉汉学而言,姜广辉总结:“清代乾嘉学者,特别是皖派学者喜爱将自己的治学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如钱大昕《卢氏群书拾补序》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又在《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称赞戴震:‘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书汪苕文书中星解后》说:‘自宋以后,儒者率蹈虚言理,而不实事求是,故往往持论纰谬。’阮元《揅经室集·自序》说:‘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又于《揅经室三集》卷五《惜阴日记序》说:‘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汪中《述学》别录《与巡抚毕侍郎书》:‘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清初至乾嘉诸儒,虽无明确的今古文经学学派的分野意识,但他们在方法学上无意识中所选择和遵循的准则,则确为汉代古文经学之潜在传统。
清代汉学之倡导者为惠栋,钱穆称:“汉学之称始于三吴惠氏。”惠栋平生治经以《易》为主,旨在复兴汉儒象数,启清儒“汉学”名义之端绪。惠栋之学,梁启超评价其“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惠栋之学于两汉今古文经学兼采,好古而少裁断,于汉代以阴阳五行谶纬方术解经之说,亦多采信;乃至坚信先秦两汉文籍中所载之古法旧制,倘行于后世,确能经世以致太平。惠栋所著《明堂大道录》是他寄托古人以表达现实理想的作品,戴震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拜晤惠栋时曾读过此书,后在与钱大昕的书信中感慨说:“晤惠定翁,读所著《明堂大道录》,真如禹碑商彝、周鼎齐钟,薶藏千载,班班复睹。微不满鄙怀者,好古太过耳。”于其过分之“好古”显有微词。章太炎更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明堂大道录》照搬汉儒的神秘主义倾向:“惠氏所作《明堂大道录》之类,颇多迷信之谈……日本人有一戏语,谓惠栋为洪秀全之先驱,我谓惠氏颇似义和团之先驱也。”虽然,惠栋之学之“好古”亦隐含“求是”之理念,他认定宋儒解经,“不仅不及汉,且不及唐”,这是因为他们“臆说居多,而不好古也”,意在破宋儒之“非”而求汉儒之“是”,但由于其经世致用理想的引导,其致思又往往无意识地切近今文经学传统,其于注《说卦传》“帝出乎震……成言乎艮”句曾道出他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愿景:“圣人居天子之位,以一德贯三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阴阳和,风雨顺,五谷熟,草木茂,民无鄙恶,物无疵厉,群生咸遂,各尽其气,威厉不试,风俗纯美,四夷宾服,诸物之福,可致之详,无不毕至。”如是云云,与近代今文经学倡导者康有为的“大同”之说,堪称前后呼应。
惠栋弟子王鸣盛曾“间与东原从容语:‘子之学于定宇何如?’东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戴震之语,道出他与惠栋之学价值向度的不同取向,也明确表达出平生宗旨唯在“实事求是”。戴震治学恪守“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之语,追求精审严密的“十分之见”,他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说:“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此一准则,实即斯后乾嘉诸儒之共识,亦河间献王“实事求是”说在清代学术中的显豁发皇。
清代后期今文经学兴起之前,乾嘉学派确无今古文之分的明确意识,但古文经学“实事求是”之宗旨,已通过他们对东汉许、郑、贾、马的认同潜在地贯通其中。晚清孙诒让揭橥古文经学之旗帜“与今文为敌”,其在《周礼正义》中谓今文家以古文经皆“莽、歆所增傅”之说,“其论大都逞肊不经,学者率知其谬,而其抵巇索痏,至今未已者,则以巧辞邪说附托者之为经累也”,并强调:“为治之迹,古今不相袭。”自谦所著“素乏经世之用”,似隐隐对今文家所标榜的复古以“经世”之说表达出不以为然之意。孙诒让认为,时移世易,古人之陈迹不可能直接作用于后世,唯有原理性和精神性的内涵,“固将贯百王而不敝,而岂有古今之异哉!”治经之目的,在于“由古义古制以通政教之闳意眇恉,理董而讲贯之”,得以“通天人之故,明治乱之源”。浚通源流以彰显历史理性,方可资今人之镜鉴,这与今文家以主观和功利性的“托古改制”的经学诠释理念,明确了根本性的分野。近代章太炎尊孙诒让为师长,更坚决反对晚清今文学者以学术为功利之术的倾向,明确提出:“学说是学说,功业是功业。不能为立了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好;也不能为不立功业,就说这种学说坏。”因为“学说和致用的方术不同。致用的方术,有效就是好,无效就是不好。学说就不然,理论和事实合才算好,理论和事实不合就不好,不必问他有用没用”。故他认为经学研究的目的是,“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强调“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反对在学术研究中掺杂个人主观情感倾向,故此,他以“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妍者媸,则失矣,使媸者妍,亦未得也”,而对于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之价值观,他甚至认为这是束缚自由思想的枷锁,“故通经致用,特汉儒所以干禄,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为桎梏矣”。这些论述,使得清代乾嘉学派的历史主义精神向度,彻底得以彰显出来。
四、余论
学界长期以来流行清代乾嘉学派欠乏思想性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张寿安、张丽珠等提出“清代新义理学”的观念进行回应,他们试图掘发清代中期的考据学者学术取向中隐含的思想向度,主要关注“情欲觉醒、礼制重建、礼教与人情的冲突、经学史学之争,以及学统、知识等问题”。实则,乾嘉之学的历史主义方法向度,其中本身亦隐含着思想方面的意义,因为“历史主义”本身就包含了其思想性。对此,我们或可从西方学界对于历史主义思潮的评价争议中,得到一些启示。
由于20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学人对于历史主义褒贬不一,因此亦导致对其进行定义有较大争议。卡洛·安东尼(C. Anthony)说:“‘历史主义’(historisme)一词独特而曲折的历程至今还没有走到尽头。这个词先后有过各种意义:最初它指的是一种错误,甚至某种反常,后来它被定义为一种积极的思想成就。”然无论对历史主义持肯定或批评态度的学人,大体尚皆接受这样一种中立的描述性说法,如弗雷德里克·拜塞尔(Frederick C. Beiser)所撰《德国历史主义传统》认为,“历史主义意味着对人类彼此间的文化和价值的一切思想还原为历史化”,而所谓“历史化”,即“意味着认识到人类世界的一切事物:文化、价值、制度、惯例、理性等,都是历史塑造的,所以万事没有永恒的形式、永远的本质或超越历史变革不变的特性。任何事物的实质都是历史所为,全然是特殊历史进程的产物”。因此,历史主义旨在立足于客观立场,辨析史料以求得历史真相,期以重建一切事物之发展和流变之历程。中国古人向有“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之论,早符斯意,以这种历史智慧来鉴往知来,观照当下,亦其题中应有之义。
总结20世纪西方学界对历史主义的批评意见,主要有三方面:首先,试图否定通过史料的辨析和实证以重建历史真实情况的可能性,认为任何传世材料都有片面性和偶然性,故以一切历史叙事都是被主观建构的“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之类。这是一种失于矫枉过正的看法。英国学者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著《捍卫历史》一书曾列举大量的实际研究经验以说明这些片面性或偶然性在严谨的研究工作中是可以被克服的,历史学家若是足够小心谨慎,客观的历史知识既是可以期望的,也是能够获得的。亦有学者指出,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正如司法人员必须依据证据以办案的情况类似。此说与乾嘉学派“以狱法治经”意思相近,如果按后现代主义者们的意见,无论历史学和司法学,都将丧失建立的合理性基础,这显然会得出一个违背基本常识的荒唐结论。其次,认为历史主义的思想向度将导致有意无意地证成“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从而甚至会顺理成章地推论出像纳粹主义之产生也存在其“历史必然性”这类结论。实际上,历史主义强调一切事物都存在其历史根源是一方面,但如何对之进行道德评判又是另一方面。兰克早年已强调人类的“道德观念等恒久不变的主要理念”是超越了时代性的,尽管某些倾向历史主义的叙事确实违背了兰克提出的这一准则,但不能说历史主义必然导向如此结果。最后,认为历史主义会导向“历史决定论”,从而独断性地推论出某些未来的“发展规律”。他们认为,未来社会的走向总是被种种偶然因素干扰,因此立足于历史规律以“鉴往知来”是绝对不可能的。此说以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历史主义贫困论》(又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为代表。其问题在于,基于宏大叙事以预测未来之“必然”确实是一种草率行为,但如果彻底否定了透过把握历史发展趋向“察微知几”“一叶知秋”的可能性,则亦属极端之论。何兆武曾批评过波普尔认定只有自然界才有客观规律,人类社会无发展规律的这一看法:“(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这个变数项也要作用并影响于自然界的;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核辐射等等。(二)至少某些重大历史事变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如在战争爆发前夕,人们可以肯定地预言战争即将爆发;战争结束前夕,人们也可以肯定战争行将结束。1944年人们已普遍地预期着战争不久就要结束了,这只是我们经验中的常识。波普尔绝对化的论点,使得他对这种常识视而不见。”此论切中肯綮。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们对历史主义思潮中出现的某些偏失之处确有敏锐把握,亦有纠偏救弊之功,但其总体论断,实在难免“过犹不及”。
清代乾嘉学者基于实证方法以“实事求是”,符合历史主义的基本精义,虽然他们鲜少“鉴往知来”之论,亦乏着眼现世的判断和批判意识,却充分发挥了旨在“去伪存真”的思想功能。他们立足于古经旧义去批判宋儒禁欲主义为“伪学”,立足于考据实证而揭示某些曾被奉为圭臬的经典为“伪经”(如阎若璩考证世传《古文尚书》之伪、姚际恒撰《古今伪书考》等),彰显出学术独立性本身的社会价值所在;而今文经学的传统一直将历史视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无论汉代今文经师称孔子“为汉制法”,还是晚清康有为所称“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托之先王,既不惊人,又可避祸”,皆是将学术与政治混而颟顸的功利主义取向,短期地看也许有其现实成效,但客观上把学术矮化成了“干禄”之术和权力的附庸,亦在学理上捉襟见肘。而古文经学传统所隐含并被清儒进一步阐扬的“求是”之精神,其虽未必直接表现出“义理”的特征,却客观上存在“义理”的向度。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著作《学术与政治》中强调学术应远离政治和功利,恪守“价值中立”的意义在于三方面:拥有“技术知识”“思维方法”和“头脑的清明”。在人文学研究领域,虽然未必存在“技术知识”,但就“思维方法”“头脑的清明”二者而言,无论汉代王充《论衡》彰显理性批判意识的“疾虚妄”,还是清代学术方法论本身的“科学精神”,为中国近代以来“现代性”之开启奠定基础并直接提供了思想资源,已经客观彰显出其历史维度的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林日杖)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姚彬彬.今古文经说同异问题争议的回顾与辨正——兼论清代乾嘉学派历史主义向度的思想渊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
姚彬彬:《今古文经说同异问题争议的回顾与辨正——兼论清代乾嘉学派历史主义向度的思想渊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6期。
本文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