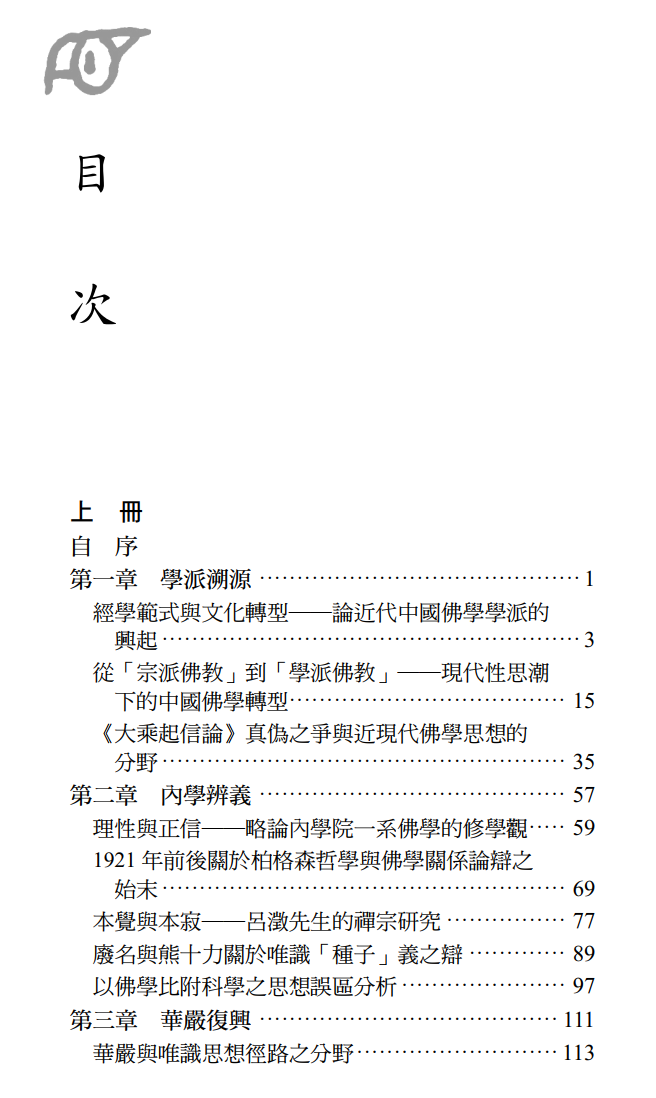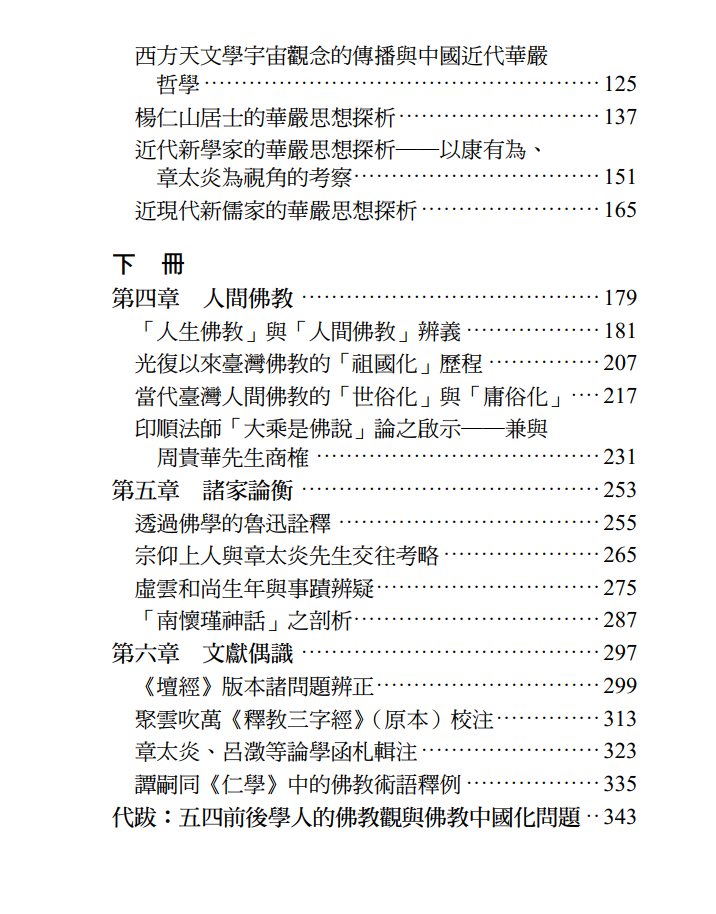中心姚彬彬副教授專著《近現代中國佛學考論》(上下卷)近期於中國臺灣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梓行,全書約四十萬字,系作者近20年來在有關研究領域成果之結集,並全面進行增補修訂。
本書提出:「近現代佛學復興」是在中國晚近思想學術界發生的重要文化現象,其所謂「復興」,並非傳統寺僧「宗派」意義上的佛教,而是「學派」意義上的佛學。擔負這一「佛學復興」思潮的主體,是出自於具有不同思想學術取向的知識精英,他們對佛學詮釋和抉擇的出發點,也往往並非是傳統意義上的「佛教信仰」,而是或將之作為接引和爭衡於彼時大舉輸入的西方思潮的中介、或將之作為寄託自身文化理想的載體。本書以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為視角,以「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為方法,梳理此一期間佛學思潮之發生脈絡,並針對個體案例和文本進行考據和辨析,涉及唯識學、華嚴學、人間佛教等相關議題,較為全面地展現出近現代中國佛學諸面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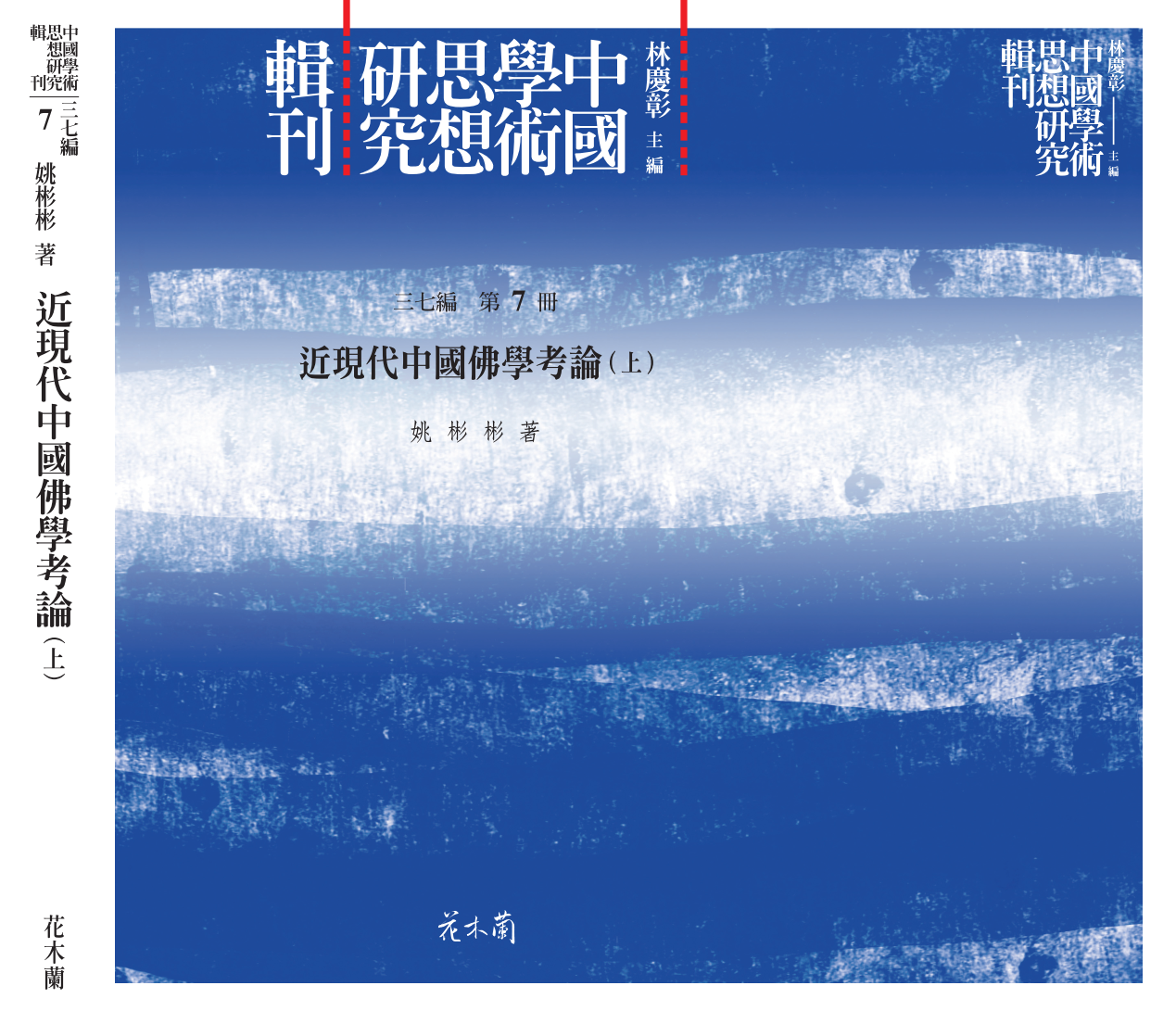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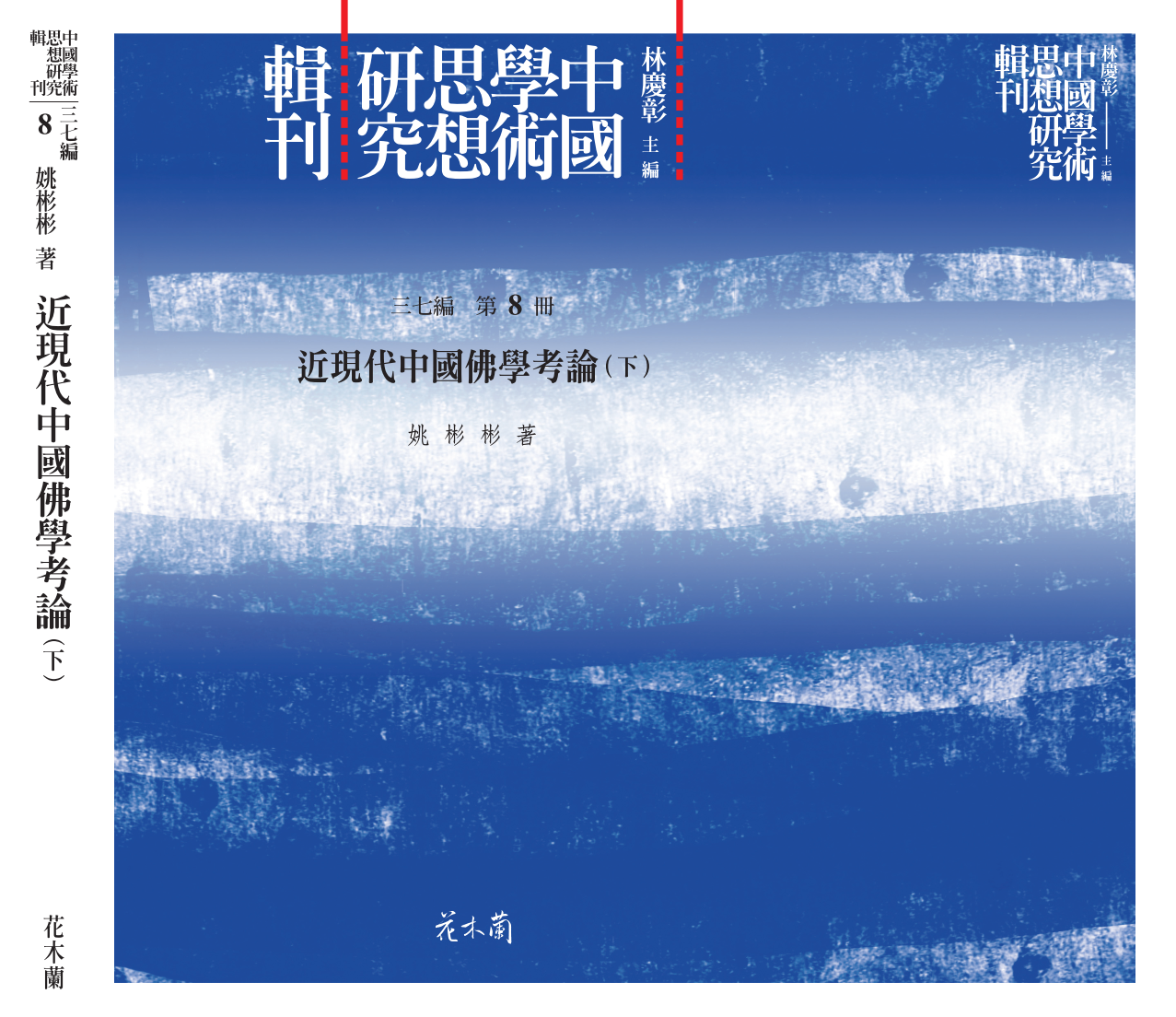
作者自序
自2001年前後開始學習和研究佛學問題,迄今逾20年。現將此期間自己尚較滿意的一些作品整理結集,對其中諸多篇目重新加以修訂。
筆者當年作為一名普通青年「打工人」,卻於近現代思想文化頗有所衷,尤服膺於章太炎、梁啟超、魯迅、周作人、胡適、熊十力諸家之說。歷時稍久,注意到所謂「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這一歷史現象,隨後日漸專注於此。2007年起,先後師從宋立道、麻天祥、馮天瑜三先生研習佛學和思想文化史,算是進入了「體制內」。
筆者最早撰寫的一篇佛學論文,曾收入已故鄭曉江教授編《一代佛學大師歐陽竟無》(2004年出版)文集中,該文撰寫於2003年下半年,學力所限,當然很不成熟,當時推薦此文發表的朋友又作了不小改動,修改處不全符合自己的想法,今已「悔其少作」。收入這本《近現代中國佛學考論》中最早的文章,是2008年所撰的《本覺與本寂》、《理性與正信》, 後者曾於該年度獲「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徵文「蓮花獎」,算是筆者初次在學界嶄露頭角的習作,此二文在當時皆由吾師宋立道先生盡心斧正。此外,《〈大乘起信論〉真偽之爭與近現代佛學思想的分野》(完成於2011年)一文是對2005年所撰的《宗教與哲學的兩難:〈大乘起信論〉義理之爭的百年回顧與反思》的重新改寫,當年蒙吾師麻天祥先生厚愛和提攜,以青年愛好者的身份攜此文參加了2006年武漢大學主辦的「佛學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也正因為天祥師勉勵有加,我才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走上學術之路。
筆者的學術方法傾向於「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思想史研究路徑,也頗有一定「考據癖」。早年間曾對唯識宗的那一套「繁瑣哲學」感興趣,故對近代佛學重鎮南京「支那內學院」諸公的佛學思想進行過一些研究;後來又涉及到近代新學家和現代新儒家的佛學思想,以及晚近人間佛教思潮的研究。2013年博士畢業後,蒙吾師馮天瑜先生獎掖,得以留校工作,最初的任職單位是本校臺灣研究所,所以又涉及對當代臺灣佛教社會現象的一些探討。一直以來,個人思想傾向較為認同人文主義和啟蒙主義,故對晚近流行的神秘主義思潮亦有所批評和反思。
近幾年,筆者的學術興趣有所拓展,研究領域逐漸轉向清代以降的思想學術史問題。於佛學研究,雖然仍保持一定關注,亦對時下的流行學風有些顯得「另類」的個人愚見:宗教研究與宗教本身的聯結越來越緊密,使得該領域表面看起來頗為繁盛熱鬧,而與之伴生的問題,則是出現了大量的急功近利的「命題作文」,甚至不乏純粹「為稻梁謀」、「結論先行」的所謂「成果」,實在利弊難言,前景堪憂。筆者一向堅持認為,人文研究,特別是在有關宗教和哲學的領域,「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無論是情感投射還是利益關係,都應該維持一定的「安全距離」,否則會傷害到「研究」的客觀性,「以水濟水」成風,必不利於學科良性發展。──作為本書「代跋」的《五四前後學人的佛教觀與佛教中國化問題》成文最晚(2022年3月),較系統地表達了筆者近年總結確立的「佛教觀」和基本學術立場。
今歲筆者適逢「不惑」之年,本文集的出版,算是對個人青年時代學術探索的階段總結, 採山之銅,以蠡測海,淺妄之處,或所難免,實盼方家正之。
姚彬彬
辛丑孟夏識(壬寅仲秋修訂),於武昌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