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华教授是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暨历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曾出版《明代宗族研究》《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等专书12种,在《历史研究》等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及各式文章340余篇,多年兼任我中心的学术委员。他主要研究中国社会史,包括相关理论和方法、宗族问题、国家与社会、区域问题等,近年来大力提倡明清日常生活史研究,是相关领域权威。
余新忠教授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暨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明清社会史和生命史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等著作4部,另有编著、译著7部,在《历史研究》《东洋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90余篇。其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是医疗史和生命史方面的权威。
关于如何理解社会文化史,常教授提出了多种思路。其一,常教授指出社会文化史存在“社会”“文化”这两个学科领域的相互交叉关系,即从社会看文化,从文化看社会。常建华教授引用刘永华教授在《社会文化史读本》中的观点认为,在阐释社会现象时需注意到其对当事人的意义和人们对于此种社会现象的看法,研究文化现象时需注意其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这样可以避免虚悬。其二,社会有修饰文化的涵义,两者并非平行的关系,而是有主次的,社会文化史侧重于文化。由此来说,新文化史就是引入社会史的涵义来探讨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史有所不同。
常教授以康熙将其书法赠与大臣为例,阐释了这一常见的礼仪行为背后折射的君臣关系。他认为康熙特殊的皇帝身份使得这一行为有了多重解读,常教授将其总结为“共赏与建构”:共赏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与臣子共同欣赏;建构则是建构权力关系为政治服务。因此他认为在社会史研究中,将社会关系网络的概念、政治史中的君臣关系以及文化史中的建构理念这三者有机结合,有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和研究问题。
余新忠教授阐释了新文化史的西方背景和学理源头,认为其更多地强调文化的建构性、能动性,是对过往历史研究中“人”的缺失的反动。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主义日渐盛行,形成了人文学科“科学化”的思潮。在此思潮下,历史学研究更多注重宏大叙事,探讨整个国家、民族甚至人类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没有个人叙事的立足之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界批判人文学科研究中缺少“人”的问题,出现了“文化”的转向,新文化史应运而生。余教授认为这也与20世纪更加注重个性解放的潮流大致同步,也就是说,新文化史是对社会新思潮和时代需求的一种回应,它促使历史学研究进一步思考人在历史中的能动性,以及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最后余教授谈到他近年倡导的生命史研究,即让“人”回到历史中来,让生命成为关注的对象。
武汉大学陈锋教授认为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对历史研究非常重要。他指出,自冯尔康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倡导社会史研究以来,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开拓之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诸如日常生活史、医疗史、生命史等新领域的进取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同时陈教授认为,跨学科的融合研究使得我们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者无论做何种研究都须多视野、多角度思考。
杨国安教授提出历史研究的三个立场,即政治史研究的国家立场、经济史研究的世界立场、社会史研究的人的立场。虽然财政史以往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国家的角度,但不能忽视了对人的关怀。杨教授呼吁同学们积极思考,例如,如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何把旧的课题做出新意等。最后杨教授指出,文化在历史研究中的功能将会越来越强大,文化如何推动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背后的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挖掘。
杨华教授也提出其关于学科界限的认识。他引用王国维先生在《国学丛刊序》中的说法,“学无古今中西”,认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值得深思。他认为,学科本无界限与差异,所谓的界限是由研究者自行构筑起来的,是一种自我限定。我们应当寻找学科之间的共同点和融合之处,而新的学术生长点往往是在学科的交叉和边缘处。另外,杨华教授也建议年轻学者不要盲目追逐“学术消费”,忽略早年前辈学者的拓荒工作。学术的发展方向总体上呈波浪式前进,因此研究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随波逐流,应加强自身修炼,建立自己的原点,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研究高度,否则将无所依归。
在讨论环节,师生们就专业学习中的困惑向两位教授积极请教,常建华教授与余新忠教授也一一给予了回应与建议。
首先,关于历史研究的主体辨析及如何将其引入历史研究的问题。常建华教授认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就是普罗大众。至于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普通人的研究视角,常教授推荐研究清史的青年学者多多研究和利用清朝的刑科题本。他认为刑科题本是一种无意识的史料,其中记录的普通人的口供,就是在为普通人发声。以之为例,常教授认为应当关注其中记录的冲突双方,立足于人的社会活动和经济现象,介入生活场景,由此复原当时的立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他将这种研究方法总结为“三见”,即“见人、见物、见生活”。
其次,关于如何看待“细节化”“碎片化”研究的问题。余新忠教授认为小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也需要立足大的框架。因此,学术研究无所谓“碎片化”,历史叙事必须置于一个大的框架和脉络中,与其防止“碎片化”,不如加强自己的研究能力,将研究的细节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展开思考。余教授特别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探讨问题时一定要追寻其背后的内在意义,学会勾连细节。
第三,如何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找寻和体察个人心态问题。余新忠教授认为,历史学研究讲究“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但进入“人”的所思所想,研究者还须拥有建立在广泛阅读基础之上的历史感、推理能力和想象力。余教授以“鼠疫”一词的历史背景为例,指出历史研究好似侦破案件,需要对细节进行推理和想象,他建议青年学者要学会观察和挖掘细节。
第四,如何在其他学科研究中引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常建华教授指出,目前在制度史研究中,学术界通常是引入在制度创建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关注制度背后“人”的互动。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就是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从这种角度来看,一切历史都是“社会史”。而就具体的研究案例或研究过程来说,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引入还是与研究本身的历史深度有关,研究者需要因时因势对自身的研究进行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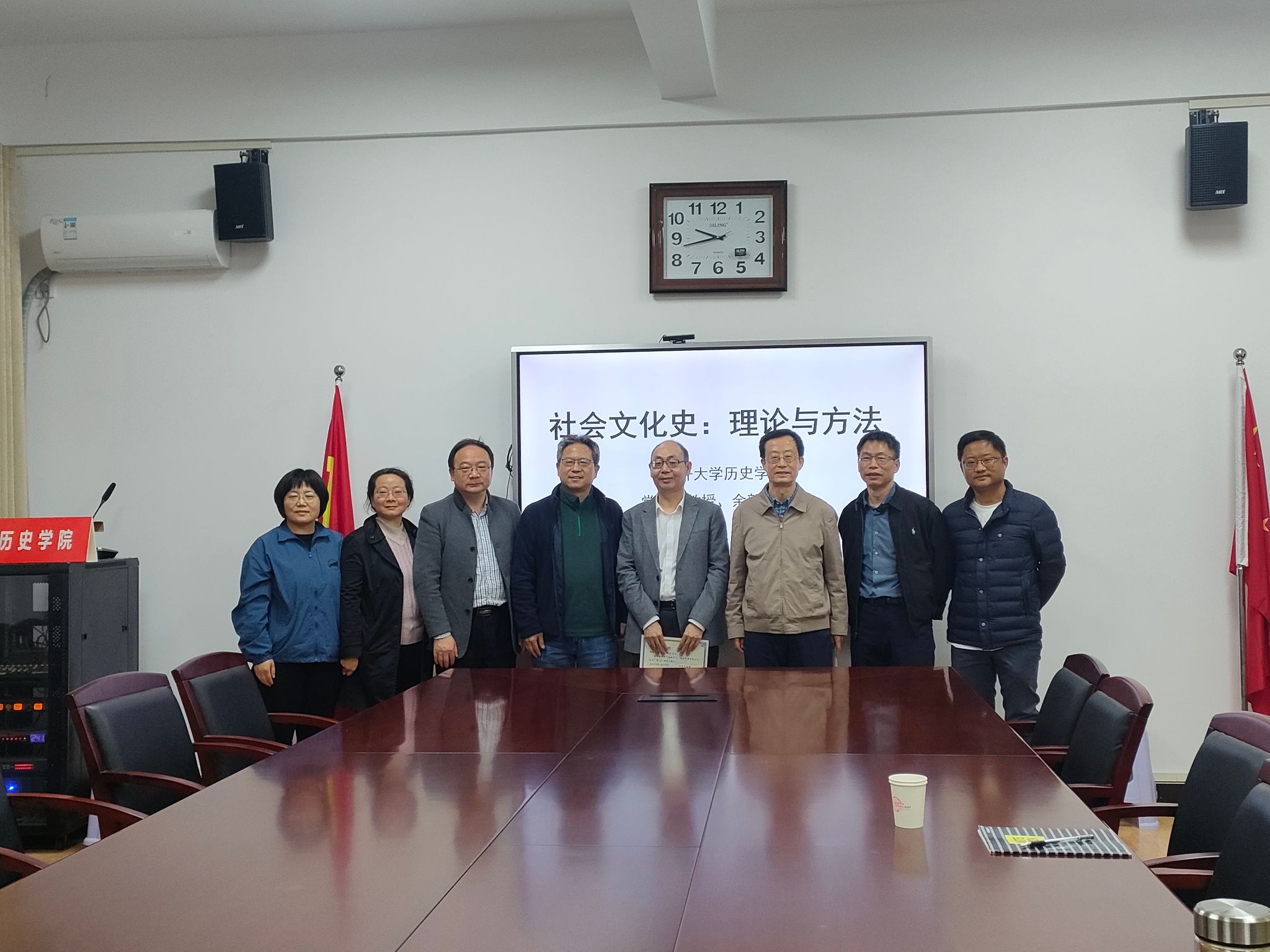
几位学者都认为,虽然存在“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等不同的理论与方法,但是“文无定式”,历史研究也没有固定的方法。希望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学们多多研究文本,互相借鉴,不要拘于一域。(欧阳阿兰、焦芹芹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