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彭国翔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壬寅年真是凶险。眼看着旧岁即将辞去,新年马上到来,就在大家终获人身自由并期盼着大疫即将结束之际,却不断听到老人离世的噩耗,各行各业的都有。前天刚刚得知中国哲学圈内一位长者过世,今天(元月12日)又突然看到了冯天瑜先生故去的消息。惊愕之余,我在微信朋友圈匆匆写下这样一段话,表达了当下的感受:“他浸润古典、深造自得,能够与近代那些真正植根于传统的知识人一样,识见明达,深悉中西文化之相通,而毫不迂腐保守,令人由衷地佩服。”但接下来的几天,我的思绪和感受一直不能离开他。
初识冯先生,是1991年他莅临南京大学演讲,讲题好像是“中华元典精神”。那次的讲座系列,除了冯先生之外,校外前来担任主讲人的学者,还有庞朴和张岂之两位先生。当时我是大四的学生,已经经过了80年代末“文化热”的洗礼,读了一些书,有了一些想法。数次讲座之后,都斗胆向几位先生请益。那时冯先生几乎是一口的武汉话,但我们交流起来,一点障碍都没有。
第二次和他见面,是1992年元月,我途经武汉时。因为要在那里由水路换铁路,为从容计,我就在朋友家暂住了两日。虽然时间并不充裕,我还是专程到他府上去拜访。记得当时他还在湖北大学任教,住处好像就在湖北大学。我是晚饭后去的,一路昏暗,还是当地的朋友带路,才找到他家。那一次,和他谈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他的夫人不仅招待茶点,也一直坐陪,间或还加入我们的谈话,非常热情。临行前,蒙他惠赐不久前刚出版的《劝学篇·劝学篇书后》点校本,至今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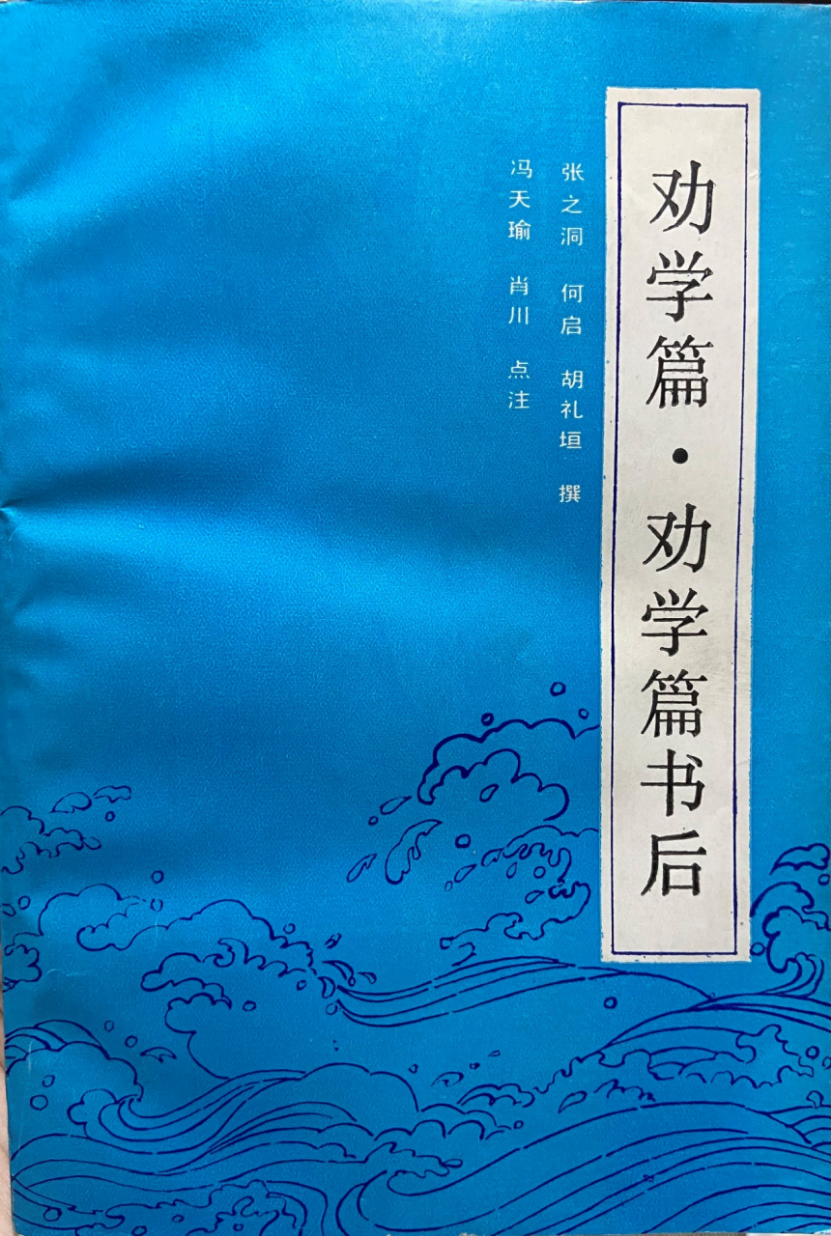

第三次和他见面,已是2006年。当时我在清华大学任教,到武汉大学参加一个现代新儒学的会议。在那之前,冯先生已经由湖北大学转任武大,创立并担任了武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大概是因为会议主要由武大哲学系操办,加之会议主题是现代新儒学,议题不在冯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之内,我记得冯先生虽然也在开幕式上露面并讲了话,但之后不久就离开了,似乎没有全程参与。因此,我那次和他只在会场匆匆一面,简单寒暄几句,未能多谈。如今想来,真是非常遗憾。因为在那之后,我们好像就再也没有过当面叙谈甚至寒暄的机会了。
尽管如此,我一直关注冯先生不断出版的著作。我对他的一些经历,也是在我1995年到北大求学之后,才逐渐有些耳闻的。可以说,我虽然大学时代和他有过当面的接触,当时已经判断他堪称中国文化史的一流学人,并对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力提倡和推崇的“元典精神”由衷认同。但是,我对他的学思能够有较为总体的判断,并格外认同和佩服他的品行和识见,却是在不再和他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之后,从21世纪初直到不久之前。
冯先生的生平事迹、学思历程以及一生著述,相信很快会有他的弟子门人整理介绍,嘉惠学林。而我作为一个年轻时曾和他有过接触、特别是曾经当面和他有过深入交流并受过他指点的后学,在他遽归道山之际,无论是在情感还是理智方面,都不能无感。在此,就让我从个人的角度,谈谈我对冯先生作为一个纯正学人的感受和看法。
记得90年代后期,好像是北大的一位师长曾经跟我提及,冯先生是被领袖人物点名肯定过的。昨日看到武大官方发布的冯先生的讣告,其中提到他曾经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度担任过武汉市委宣传部长,但为期仅三年。今日看到熟悉他生平的人士在回忆和纪念文字指出,冯先生当时是主动辞职的。而和此事彼此印证,颇能说明冯先生价值取向的,则是好几篇文章里不约而同都提到的:冯先生不仅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再拒绝“进京任职”,80年代在湖北大学期间,更是两次拒绝担任校长的任命。如今看来,冯先生70年代后期担任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应当与昔日领袖亲点其名有关,可以说是被推上去的。但他很快主动辞职,并拒绝在很多人看来难得的进京任职的机会,显然说明国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在冯先生的价值系统中是没有地位的。他两次拒绝担任校长的任命,更是毋庸置疑地表明:在他的意识中,如果也有一种“本位”的话,那显然是“学”而非“官”。这一点,其实正是古今中外纯正知识人的本色。
有人提及,“远权贵,拒妄财”是冯先生的家训。冯先生“远权贵”这一方面,从上述事迹来看是毋庸置言的。而最能反映他“淡看金钱”这一方面的,则是他将极为丰富和珍贵的家藏文物和艺术品包括古币、书画等悉数捐出,而非出售给海内外一再联络他的商家。既然是“家训”,当然意味着冯先生的价值观受其父辈和祖辈的影响。对此,也有人溯及冯先生的家世,尤其是他的父亲冯永轩先生对他的教诲。冯永轩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研究生毕业,师从黄侃、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生前曾任武汉师范学院史学教授。如此看来,家风家学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不过,我想说的是,家训固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冯先生自觉选择“学本位”,拒绝“官本位”,更是他在自己生活的世界和年代里所做出的一种属于他自己的“存在的抉择”。而这一“存在的抉择”,结合他21世纪以来不断的学思进境,尤为让我感佩。
不知什么时候,“与时俱进”成了流行话语中一个几乎人尽皆知的词汇。不过,这个词的本来涵义是什么,很多人就未必知道了。“与时俱进”一语,出自蔡元培先生1910年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所谓“故西洋学说则与时俱进”,大概是概括中国古典中“与时偕行”、“与时俱化”、“与时俱新”等用语而成,针对的是晚清中国社会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风气。就此而言,如今回顾其学思历程的话,在我看来,当今之世,冯先生可以说正是能够真正体现这个词汇本来涵义的为数不多的学人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开始不再作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但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批判和否定之后,中国传统文化虽未被某种新的文化完全取而代之,但对于广大国人来说,其实已经较为陌生了。尽管80年代之后逐渐解冻,90年代在思想界初露端倪,但直到21世纪之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正面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才在全社会范围之内展开。我还清楚地记得,90现代初期,大学校园里占据主流的仍然是西方的各种思潮,中国传统文化虽然随着“文化热”已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但还远远没有达到21世纪以来那种流行的地步。如此看来,冯先生在90年代西方思潮仍居主流的情况下,便呼吁“中华元典精神”的重要,显然是真正“与时俱进”精神的体现。
“中华元典精神”是1992年元月我在冯先生府上听他谈及的主要话题之一。所以,对于他20世纪90年代初的“与时俱进”,我可以说是亲身的见证者。后来,我虽然没再有机会向他当面请益,但透过阅读他的文字,对他“与时俱进”精神的印象却不断加深,直到突然看到他去世的消息。
如果说“与时俱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创新”,正如孔夫子所谓“温故知新”,真正的“创新”一定要建立在对于以往经验全面与深入的掌握这一基础之上。冯先生在2006年初版的力作《“封建”考论》,就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历史教科书的长期影响,把秦汉以迄清代中国漫长的历史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已经深入绝大多数人中国人的意识。不仅如此,“封建”也成了一个负面价值的形容词。以至于说一个人“封建”,就等同于说一个人保守、落后乃至愚昧。但是,“封建”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个绝大多数人从未反省的词语,冯先生的《“封建”考论》可以说给出了最为全面和可靠的回答。当然,对于是否可以将由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定义为“封建”社会,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界,已经有一场大规模的论战。那个时候,套用某种未经检讨的“舶来品”而将由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定义为“封建”社会,反而不占主流。冯先生对“封建”的检讨,不仅充分吸收了20世纪30年代思想论战的既有成果,更在此基础之上做出了更为全面和细致的分析与论证。
他的一些判断,例如:“将君主集权的秦汉以降中国社会冠以‘封建’名目,此‘封建’与封建之古义(分封建藩)和西义(封土封臣)双双脱钩,既失去历史依据,又缺乏比较参照。”“秦汉以降两千余年社会的基本面并非早已成为偏师的‘封建制度’,秦以下诸朝代虽仍然封爵建藩,但主要是‘虚封’,而并非‘实封’,受封贵胄‘赐土而不临民’,‘临民’(对民众实施行政管理)的是朝廷任命的流官。列朝也偶有‘实封’(如汉初、两晋、明初),很快导致分裂(诸如‘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役’),朝廷又大力‘削藩’,强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秦至清制度的基本走势是——贵族政治、领主经济被专制政治、地主经济所取代,其主流是一种‘非封建’的社会。从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到钱穆、梁漱溟、李剑农、费孝通等注重中国历史自身特点的学人,一再阐明此点。中国前近代社会形态,从大格局言之,由经济上的地主-自耕农制、政治上的专制帝制综合而成,其社会形态呈非封建性。马克思、恩格斯深悉此中精义,综览其全部论著可以得见,唯物史观创始人从未将前近代中国称之‘封建社会’,而以‘专制社会’、‘东方专制社会’相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以及“中国的‘封建制’行之殷周,与‘宗法制’互为表里,故殷周可称之‘宗法封建时代’,承其后的秦至清两千年,可称之建立在地主经济和专制政治基础上的‘皇权时代’。”可以说堪称“温故知新”的极佳范例。
历史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一说法在国内甚嚣尘上。对此,冯先生并没有顺俗浮说,和一些浅人一样陷入盲目的自我陶醉之中,反而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以及对世界格局的充分认识,提出了清醒的忠告。这里,我只引用2013年《文艺新观察》第2期“走向文化自觉——冯天瑜先生访谈录”中他说的两段话为证,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第一段是:“‘21世纪为中国世纪’说,当然是一个令国人欣然的估量,但诉诸理性审度,又颇为可疑。此说的不恰当在于,混淆了‘大国’与‘强国’的界限。以广土众民、经济总量名列前茅而论,中国当然是世界大国,然而却不能说是名列前茅的世界强国。世界强国必须科学技术领先,占据国际经济链的上游,政治稳定高效,军事实力强大,文化具有世界感召力。时下中国与这些指标皆有明显距离。建设世界强国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愿景,尚不是现实存在。”第二段是:“需要切记,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当下及未来一个长时期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仅以农业劳动生产率这一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而言,2010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约为中国的60倍。处在这样的较低端的基点上,中国远未完成‘追赶’任务,应当扎实做好各项脱困工作,纾解危机,使中国社会走上长期正常发展的坦途,而绝不要自我膨胀,迷惑于‘21世纪是中国世纪’说的幻觉之中!”
2013年,中国经济仍在一路高歌猛进,并未显出衰退的迹象。国人大都信心满满甚至手舞足蹈,听到冯先生的这两段话,恐怕很难信服。然而,将近十年之后的今天,再来重温冯先生的这段话,我个人觉得恐怕非“振聋发聩”四字不足以当之。可以说,这是其“与时俱进”精神的又一个鲜明例证。
我相信,冯先生勤于史学专业著述的同时,一直不忘国计民生。并且,他所密切关注的,不仅是中国社会,还有世界大势。正是基于他深厚的史学素养,又能够将中国置于世界文明的整体之中审时度势,冯先生“与时俱进”的特点,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又有新的表现。例如,在2020年3月18日“锐角网”发布的“通过这次危机推动社会启蒙”这篇文字中,冯先生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对于当今局势做出了极为中肯的观察,同时也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了他个人的期许。
基于“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这两个有着充分经验案例为基础的观念,冯先生对当下的中国提出了两点观察:其一,“中国时下正面临此种困局:经济起飞初期劳动力、土地价格低廉等优势逐渐丧失,进入新世纪以后,产品价廉不如更落后国家,先进技术还赶不上发达国家,商品竞争力下降,如果国内经济、政治举措失当,便会落入经济缓进甚至衰退陷阱。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对此种危险估计不足,陶醉于‘厉害了我的国’的颂声中。这是要反省并改进的。”其二,“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上就讲究‘厚往薄来’,外国喜欢派使者到中国来得好处。这种以厚赐得友的外交行为应该改变。中国要确立平等互利的现代国际关系意识,不要以天朝上国姿态漫撒千金。那样做自己损失巨大,也交不上真正的朋友。”在这样的观察基础之上,冯先生对于未来提出的期许是这样的,他说:“对中国未来的期许,就是设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吾土吾民的福祉所系。更高大上的梦想,我就不去虚拟了。”显然,冯先生的这番话可以说是紧扣时代脉搏而发,同样是其“与时俱进”的表现。
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冯先生“与时俱进”最近的文字,大概是2021年元旦发表的“‘史剧’与‘史观’”这篇文章了。冯先生去世之前,我并没有看过这篇文章。正是这篇文字,连同上面提到的他的其它著作,让我对他的认识和敬佩又多了几分。
冯先生撰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动因,应该是他观看电视剧《大秦赋》之后的有感而发。文中要点有二:一是对于历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大一统”观念提出反思;二是对秦始皇所代表的专制极权做出批判。我阅读此文的第一感受,是冯先生笔端犀利,情见乎词,似乎与我以往印象中他一贯的温和气象颇有不同。然而,读罢此文之后,我立刻明白了冯先生为何会对《大秦赋》这样的影视剧有如此的反应。这实在是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民众的福祉念兹在兹的肺腑之言。如果没有一腔热血和一片公心,即便有如冯先生一样的学识,也是写不出这种文字的。正是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数不清的明枪暗箭。有人甚至破空大骂,给他扣上了“歌颂国家分裂,顶礼膜拜西方文明”的大帽子。据悉,在2021年之前,冯先生经历了数次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折磨,甚至几度踏入鬼门关。我想,有了如此经历之后,冯先生恐怕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又岂会在意一般世俗担心的因言获罪、得失荣辱呢?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王阳明“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的诗句。我想,在冯先生书写“‘史剧’与‘史观’”的时候,他必定和阳明先生具有同样的心境。在那样的心境之中,他文中所写,必定是他所坚信不疑的。他对“大一统”观念的反思,所谓“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并非在政治的分合,而在文明的进步,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进步与否。将历史的正义性简单归结为政教是否大统,必陷虚妄。”以及文章最后“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这句点睛之笔,可以说既是他一生学思淬炼所得,更是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向世人表露的内心坚定无比的信念。这两句话是如此的掷地有声,我想会在无数人的心中引发强烈的共鸣。同时,我也相信,冯先生的这番话,可以说已经“与时俱进”到了当今时代的最前沿。
在对冯先生的攻击和谩骂中,有人以冯先生1975年出版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来做文章,指责他“朝秦暮楚”、前后不一。其实,一个学者的可贵,并不在于一成不变,而恰恰在于能够在不断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和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像梁任公那样“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这才是蔡元培先生“与时俱进”一语的本义。而能够做到这一点,没有不断积累、日趋深厚的学养以及“不诚无物”的道德勇气和自我批判精神,是断然无法做到的。就此而言,从1975年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到2021年“‘史剧’与‘史观’”中的“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祖龙魂死二世亡,孔学名高万载长”,正见出冯先生精神蜕变和发展的历程与其结穴所在。这一点,也正是冯先生令人敬佩的一个重要所在。
我和冯先生行迹交往并不多,正如前文提到的,2006年之后,我大概就和他再无面对面交流的机缘了。但是,正如古人所谓,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大体有“水”和“油”两种不同的形式。学人之间的彼此了解,原本更多地是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而不在于江湖流行的觥筹交错。不然的话,庄子“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之说,便不会历来被学人视为相互了解的最高境界了。冯先生所建立的宏富的知识世界,我不敢说已窥宫墙之美;但冯先生毕生学养淬炼最终所得的“识见”、“价值”和“信念”,我相信在我心中具备强大的“同情”与“共鸣”。如果冯先生生前偶然也看到过我这些年的一些文字和议论,而能颔首微微一笑,对我来说,十几年来未再促膝而谈的遗憾,也许会释然不少。
谨以此文纪念冯天瑜先生!
2023年1月12日动笔,17日写毕